头疼欲裂,太阳穴和心一起烦躁。
我在黑夜里睁眼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时间概念,只觉得脑袋旁边有什么声音在隐隐约约拨弄着空气,像是深夜后没有频道的电视,频率恼人。那个声音慢慢清晰的时候,也是我被它完全吵醒之时,我厌烦地翻了个身,右手够到枕头旁边的手机。
3:20,调到最低亮度的屏幕上两只浅金色的鹤在主界面上展翅,我以为它们在飞翔,但是定睛后,才发现它们可没我头顶的小生物那么活跃——说起那个小生物,它还锲而不舍地在我周围,声音忽近忽远,我能想象到它在黑暗里打转。
转来转去不会头晕吗?我愤恨地又瞥了一眼时间,把手机锁屏。
嗡嗡的声音再度袭来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,每当蚊子离我近一点时,那越来越大的声音刻意地激起我好厚一层鸡皮疙瘩,然后我便是反射性地扭动身子并配上双手在空中胡乱挥动,像要吃药的不听话的孩子。它来了,我便如此,它走了,我就乖乖地侧身缩着。来来回回好多次,我被整得一身汗。
汗像是玻璃上隐隐的雾气,不会顺着玻璃下流,只是安安静静地贴在那里。那一层薄薄的黏湿感就这样罩在我的身上,我无法擦拭掉,只能任由它留给我的触感在全身蔓延开来。这种情况下蚊子再出现时,我只能烦躁地发出一阵鼻音,然后翻个身。
所以我越来越清醒,像准备跑八百米的胆小女生。
不知是心理作用,还是蚊子在黑夜中终于捕捉到猎物,身上痒痒的感觉逐渐似潮水般层层袭来,瘙痒感和全身粘稠的热意让我登时感觉自己被抛到了海里——也可能是我自己跳进去的,毕竟水至少能带来一丝凉意——如果可以。海水咕咚咕咚,犹如吐泡泡一般翻着水波,我的鼻孔和嘴巴里也往外往里传递着海水。实际上我也分不清水是往外还是往内,我只因为堕入海中有些恐惧和烦闷,毕竟我不会游泳。
我之前以为“跳进海中”会凉快一些,可是那水似是温热的,像煮青蛙的温水一点点地往上散发着热意。我躺在床上,感觉周围“海水”的热将要超过武汉的夏天,将要在一场温度的角逐中获得胜利,它和入夏的武汉都是恶魔,尝试用自己的歪门邪道让深夜中的人们不得安眠,只不过这“海水”似乎更加老练一些,懂得用自己的样子诱惑人们归顺于它,结果只能是让人们更加烦闷不得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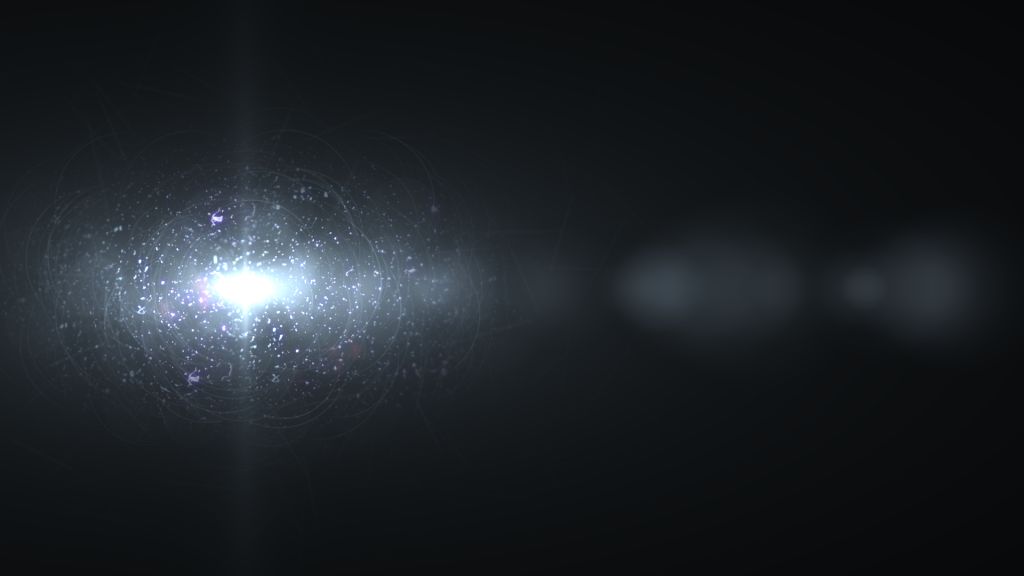
我心里面冷哼一声,觉得武汉的夏还是太年轻,不懂迂回之道。既然如此,我也只能逃回到失败者的怀抱,少受一点整蛊。
我睁开眼睛,快四点,跳下床跑到走廊的尽头洗把脸,顺便把胳膊放在了水龙头下方冲着,凉水在皮肤上蔓延,下坠,然后又在瓷砖台上汇聚流走,我总感觉,这里的水,才是我印象中的海。
回到床上的时候,手臂上的凉意还没有散去,没完全干的皮肤蹭到脸颊和脖子上,格外舒坦,我翻了个身,确保自己摆好了最舒服的姿势,终于准备睡下。这时全身上下都是舒服的,舒服得想立马睡着。
只是还有一个问题。
暑热尽消后,不一会儿那熟悉的声音再度传来,说来也怪,它似乎钟情于我的被窝一样,任凭我如何对空气拳打脚踢战斗不止,还是执着地在我的头顶。它就像不太会跳舞但是一直在练习的小男生,手脚不协调,但还是不肯放弃。嗡嗡的声音像是男生没跳好舞的抱怨声。
没准,它在和我一起烦躁着。
说起来也怪,我感觉它越来越像我的同类,只不过在生存和谋求所需中容易彼此伤害,给对方的心上,尤其是我的精神上挂点彩。
最后一次看表,五点过几分,我可能已经把一整晚献给了爱好战斗和竞争的暑热,以及锲而不舍“个体理性”的蚊子,我依旧特别清醒,准备下一次稿子就写“蚊子与暑热的幻想”。
虽然现在打字的我也依旧坐在空调下挠着自己的蚊子包,但是至少已经为它们和我的光荣一夜真的写了一篇“颂文”。我将要停笔,那晚的思绪也慢慢结束,当时依稀感觉嗡嗡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,可能是因为它已困倦,也可能是因为,多次打转后它也终于放弃。
醒来后的我,身上蚊子包屈指可数,实在不能算是蚊子丰收胜利,那这是暑热的胜利吗?我总觉得,其实都否——
这不过是人类对于厌烦的夏天必然的挣扎和反抗罢了。






 源自华中大学迁西版校报
源自华中大学迁西版校报